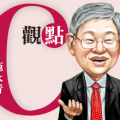制裁伊朗與安提戈涅的隱喻
接連多日介紹了滯留在伊朗的阿富汗難民的情況,有朋友好心提醒我,不應如此高調地讚揚伊朗的難民政策,還呼籲捐助聯合國難民署去支持伊朗政府落實他的難民政策。他說,他有一個朋友只因去過伊朗旅行,在入境美國時也被盤問了三個小時,我這樣做,可能會像孟晚舟那樣,在途經與美國有引渡協議的國家時,被抓起來,送回美國受審。
朋友的這番話,使我想起西方文明的一個不解的隱喻——安提戈涅的怨憤。我的處境與安提戈涅當時的差不多,就是我應該遵照上帝的旨意行事,還是服膺世俗權勢制訂給我的規限行事。安提戈涅是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塑造出來的一個形象,被公認為戲劇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。劇中描寫了伊底帕斯的女兒安提戈涅,不顧國王克瑞翁的禁令,要將自己的兄長波呂尼刻斯收屍安葬。但波呂尼刻斯卻是因背叛城邦而戰死沙場的。國王因波呂尼刻斯犯了叛國罪而禁止她這樣做。但安提戈涅卻堅持要這樣做。國王於是把她囚禁起來,導致她為此選擇自殺,最後國王克瑞翁亦悲劇收場。
安提戈涅在質疑國王命令的時候這樣說:「我並不認為你的命令如此強大有力,你只是一個凡人,竟敢僭越諸神不成文卻永恆不衰的律法。不是今天,也非昨天,諸神的律法永遠存在。」安提戈涅認為,安葬死者,尤其是自己的兄長,由來已久,大家都會這樣做,諸神也不例外,應屬自然法(Natural law)。而由世俗權力制訂出來的只是規範法(Normative law)。她認為前者更應該遵守。但現實世界卻由世俗的權勢所把控,違反規範法,必遭權勢懲罰。可是上帝卻甚少會對此進行干預,導致人間要不斷出演安提戈涅式的悲劇。
在我看來,我願意扶助流落伊朗的難民,完全是基於對受苦難的人的同情心,這種情懷是天生的,它超越我個人意識所能控制。我相信只有神的旨意才能令我不能自已。所以我只能遵守神的意願,而不顧美國訂立的,強加在別國人民頭上的強權法。
美國完全有權基於自己國家的利益,或基於歷史上的種種原因,決定制約伊朗;但美國無權強制其他國家也這樣做,美國的總統與議會是美國人選出來的,所以他們可以為美國制定規範法,而美國人必須遵守。但這些規範一離開了美國的司法範圍就不應再有效。
當然,美國仍然有權一併把與伊朗交往的國家也加以抵制;凡是與伊朗做生意的,以後就休想與美國做生意。美國或許憑着自己的實力地位,已足以令很多國家就範;但這並非美國的合法權力。我作為一個有自由意志的個人,仍有權選擇去資助流落在伊朗的難民,美國政府不是我選出來的,我並沒責任遵守美國政府訂出來的規範法。美國政府有權因而拒絕我入境,但沒有權因而拘捕我。同樣理由,美國只有權自己抵制華為,卻沒有權因華為與伊朗交往而拘捕孟晚舟個人。
(轉載自am730C觀點2018年12月19日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