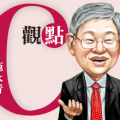我為何會關注國際難民問題
這次隨聯合國難民署訪察伊朗的其中一個重點活動,是與難民自己組織起來的自助組織成員座談。他們全都是非政府組織,有的有宗教背景,有的有地區背景,有的來自同病相憐的弱勢社群,有的純粹是基於人類的同情心而組織起來去扶助比自己更不幸的人。他們大部份都是志願工作者。
這個座談會,令我對人類的前景重燃希望。因為我看到,並非世上所有的人都只曉得爭奪資源,或為了一些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互相仇視,甚至想置人於死地。人類的本性中,亦有善良與慈悲的一面。這些阿富汗的難民,本身的處境亦不是太好(一般香港人都比他們生活得好),但他們仍願意撥出資源——主要是時間,為受苦難的同胞服務。
有一對失明的姊妹,因懂一點樂器,常為難民同胞舉辦的活動表演助興。開始時只是義助,後來也可以收到一些報酬。他們把部份這些新增的收入組織NGO,專門幫助身體有殘障的難民。可能正是因為她們自己的不幸,令她們更了解不幸人士的需要,所以更願意伸出援手。
在座談會期間,我問他們為甚麼身為難民,在自己的生活都未太好的情況下,都願意捨己為人,令其他人可以生活得好些。誰知其中有位年輕的女士,很有智慧地反問我,為甚麼在香港活得好地地,要跑到老遠,來關心非我族類的阿富汗難民,好想先聽聽我的答案才回答我。
其實這個問題我之前並沒有好好地想過,我只是按自己的感覺,憑自己既有的條件去做事,沒有把自己的行為上升到理論層次。她的反問令我不得不深入地去思考這個問題。
我自小就對受苦難的人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同情心,在上世紀五十年代,香港路上有時候會看到棄嬰。我聽到他們的哭聲,知道他們尚未死;我看到他們是用被包得好好的,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寄望有人把他們抱回去的。我總有一種衝動,想把他們抱回家去。但我知道,我父母自顧不暇,是不會容許我這樣做。所以我想,他日我長大後,如果有能力的話,一定會盡量去幫有需要的人。
其實,香港人大部份都是難民,或難民的後代。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,令很多中國人都要流離失所,遠走他鄉。我當年亦是因此而隨父母從上海流落到香港的,人地生疏,語言不通,物資貧乏,生活不穩。所以對難民的處境很容易理解,容易產生同情心。所以即使在我的生意尚未做起來之前,我已參加了多個慈善機構,捐錢或做義工,希望多少能盡點綿力。
我很認同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Filippo Grandi的說法,如果我們對全球的難民問題無動於衷,世界將不會有和平,人類社會亦不會真正富裕起來,人們亦不會有幸福的生活。我相信人類的DNA裏,既有自私為己的求生本能,亦有利他的為群體作犧牲的衝動,兩者並存,人類才可以建立起以個體為基礎的群體社會。人類要有美好的明天,不能只講自利,不講利他。此之所以,阿當·斯密除了著有《國富論》外,還著有《道德情操論》。前者崇尚利己,後者主催利他。只可惜大部分人都只知道前者,不知道還有後者。
(轉載自am730C觀點2018年12月17日}